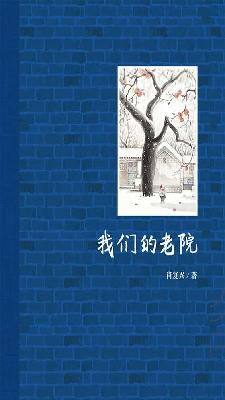,叫粤东会馆。那是一座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会馆,坐落在北京城前门楼子东侧一条叫作西打磨厂的老街上。清光绪《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记录那时在这条明朝就有的老街上,有粤东、临汾、宁浦、江西、应山、潮郡六大会馆,粤东会馆名列第一。到了北平和平解放之时,这条老街上的六大会馆,仅存粤东和临汾两座。从落生到去北大荒插队,我在粤东会馆里生活了二十一年。
我们大院里,住着各色人等。尤其是老一辈人,表面波澜不惊,却身世如乱云,人生似飘蓬,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从童年时光里那些老人欲说还休遮遮掩掩的神神秘秘,到“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家庭都被无情地撕开一道口子,让很多神神秘秘的往事变成了触目惊心的现实。这些活生生的人与事,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人到晚年时,蓦然惊醒,变成我写作的财富,有了《》这本书。
纳博科夫曾经说过:“任何事物都建立在过去和现实的完美结合中,天才的灵感还得加上第三种成分:那就是过去。”过去的作用,对于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巨大。在时间的作用下,过去有了间离的效果;在想象的作用下,过去成为写作的酵母。于是,人生不仅是人生,还可以是文学;不仅可以让我们回忆,还可以让我们品味。杜诗云:“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便是让我品味我们的人生、品味的路标和路径之一,自古如此。
因此,,写的是粤东会馆,已经不完全是粤东会馆。那里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曾经生龙活虎真实地生活在过去的年月里,却也生活在我今天的想象里和重新的构造里。为了更加真实,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对号入座,那些人物,我进行了张冠李戴,甚至偷梁换柱,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可以说,我今天笔下的,是地理意义上的粤东会馆,是历史意义上的粤东会馆,也是文学意义上的粤东会馆。它是为粤东会馆写传,也是为写意。它属于那条已经被破坏被腰斩或者叫作被改造更新的老街,更属于我们,属于我自己。
正如纳博科夫所说的过去对于现实的重要作用,要想真正走进,重新梳理一下粤东会馆历史的空间和地理的肌理,也许还是很有必要的。
据我所知,在北京城,以广东或广东各地方名字命名的会馆有很多,比如新会、蒲阳、潮州、惠州、肇庆等会馆,真正被称之为粤东会馆的,自有会馆以来,只有三家。
先说第一家和第三家。第一家建的最早,第三家建的最晚。
第一家在广渠门内。据我的同学王仁兴1984年考证,这第一家粤东会馆开始叫作岭南会馆,是旅京的广东同乡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的。北京第一家会馆,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当时一位在史局任职的官员首议兴创,在菜市口建的安徽会馆,也就是说,第一家粤东会馆比它只晚了六年,当数北京最早的一拨会馆,历史很悠久了。
当年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广渠门激战后金军,不料背后让人捅了一刀,崇祯皇帝偏偏听信了小人谤言,袁崇焕被诬陷而在菜市口凌迟处死,其骸骨最早就是广东乡亲偷偷埋在粤东会馆里的。以后袁崇焕祠(现仍在)是在粤东会馆附近建的,那是清朝的事了。袁崇焕无疑给最早的粤东会馆抹上了最光彩也最神奇的一笔。可惜,这座最早的粤东会馆,明末的时候就已经毁掉了。
第三家粤东会馆是在南横街的东北角,它建成于清末。依然是广东同乡出资,买下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父子的怡院一角,占地六亩,比最早的粤东会馆大出几倍。显然,广东人越来越有钱,在朝廷里越来越有势力。而且,那时的广东人如现在的北京人一样格外关心政治。戊戌时期,保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变法的风云人物康、梁等人都曾经出入这里。民国元年,孙中山来京时的欢迎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他们都是广东人。想那时,出入这里的都不是庸常之辈,个个心怀百忧,志在千里,且吟王粲,不赋渊明。可以说,那是三座粤东会馆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这种辉煌,一直延续到北平解放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为开通菜市口南北大道,南横街以西被拆了一片,占据南横街东北角的粤东会馆首当其冲。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曾经提出手下留情,希望能够保住粤东会馆。其实,只要让新修的大道稍稍拐一个弯,就能将这座老会馆保下了。但是,老会馆没有新大道值钱,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短浅。
2004年,我曾经专门去那里寻访旧址,那时候,还能看到一点粤东会馆残留的影子。因为它大门外的一株老树还在,而它的邻院虽然破败,却也还在,依然可以让我想象一点它的前生前世。前不久,我又去了那里一趟,却连这点想象都没有了,新建的楼房,挤压得南横街接续往西缩,一直快到粉坊琉璃街了。想当年,拆这座粤东会馆的时候,是将梁柱等建筑材料都按编号拆下的,政府曾经允诺以后将粤东会馆和连同拆掉的前面不远处珍稀的过街楼,一并异地重建。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异地重建的事,无人再提,人们的记性真有点儿撂爪儿就忘,这座最为辉煌的粤东会馆也就如此风流云散。
下面再来重点说第二家粤东会馆。之所以重点说它,是因为这就是呀。
这座粤东会馆建于明末清初,老门牌是西打磨厂179号,新门牌90号。当时,广东同乡嫌广渠门那里的面积小,而且偏僻,交通不方便,出资迁到西打磨厂,紧靠皇城,占地两亩,盖了这个新粤东会馆。想那时的广东人和现在一样,能折腾,起码是赚了钱,要不怎么能够置办第二房产?新建时将粤东会馆曾经一度易名为嘉会会馆,后又改了回来,足见对粤东会馆的钟情。我住的时候,会馆肯定是清末民初时翻修的了,不过基本格局未有大的改变。据说,清光绪年间,广东人陈伯陶写过一副怀念袁崇焕的对联:粤峤星辰钟故里,蓟门风雨引灵旗。专门送到粤东会馆保存,可惜,我问过老人,谁也没有看到。
它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街旁的高台阶上,两大扇黑漆木门,两侧各有一扇旁门,虽然破败,但基本保留着当年的风范。大门内足有五六米长的宽敞过廊,我们叫它大门道。过廊里西侧有一大间房子,有门无窗,是当年的门房。东侧有一块贴在墙上的黑板,是抹在墙上的水泥,再刷上一层黑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产物。当时,在上面写着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语录。有意思的是,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好多年之后重访大院的时候,不仅它还健在,而且,上面用粉笔书写的语录也还健在。有趣的是,那语录正是当年我写上去的。小二十年过去了,喧嚣不再,笔迹犹新。
过廊外是宽阔的青砖铺就的甬道。其东边一侧,有一个自成一统的小跨院,小跨院里,一排三间倒座房,两间西房,两间南房,想应该是当年乡里一些赶马车的下人住的地方。西侧是一片凹下一截儿却很开阔的沙土地,是用来停放马车,让马匹休息蹭蹭痒打打滚的场所。最早的时候,那里曾有一棵垂杨柳树。我小时候,那里还是可以踢球的操场,可见足够的宽敞。方砖甬道,高于东西两侧,甬道的下面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大坑,上铺一块大木板,下面藏有全院的自来水表,捉迷藏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常常藏进去,就像电影《地道战》一样,谁也找不着了。
然后,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第一道院门,中间是有盖瓦的墙檐和牌坊式的门柱组成的院门,按照老四合院的规矩,它应该叫二道门,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它的两边是骑着金钱瓦的院墙。迈过院门前后几级台阶,迎面是一座影壁,影壁东边是一片空地,西边是一座石碑,写着好多人捐资重修粤东会馆的名单和缘由。再往里走,是以坐北朝南正房为中心的三座套院,与大门和影壁对照,中心稍稍偏西一些。除第一座院(我们叫它前院)有了前面的二道门,不再设门之外,其余两座院即中院和后院,各有朝东的一扇木院门,一为方形门,一为月亮门。
这两座院内,中院种有三株老枣树,后院有东西两块花圃和一架葡萄架,后院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很窄,我们称之为夹道,里面种着两棵桑葚树。这是里最好的房子,后院幽静,仅住两户人家,还是亲戚。中院最大,不仅有东西厢房,还有和前院正房背背相靠一排三大间的倒座房。
前院那三间正房,最早是房东住,他是广东人,是不是最早粤东会馆主人的后裔,我就不清楚了。大院已经多次易主,他应该是大院最后一任的房东了,后来院子交了公,归房管局管理修缮,他们一家依然住在这里。应该说,房子不如中院和后院的正房,我不知道为什么房东自己住。相比较,前院显得要局促一些,因为没有院门,正对着影壁,但是,前面的空间还是不小的。它有宽敞的走廊和高台阶,左右两侧各种有一棵丁香。小时候,我们常从家里拿出床单或被单,挂在两棵树之间,成为我们演戏舞台上的幕布,舞台就在房东房前的高台阶上。房东家人很少,人很和善,不管我们,任我们在那里连唱带跳地折腾。
我小时候,大院的西厢房已经没有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大符合这样三进三出四合院的建筑格局。正规的大四合院,三座院落自成一统,三座院落的外面,是应该有东西两侧的厢房的,更讲究一些的,还会有环形的游手走廊连接。粤东会馆纵使没有那样的讲究,起码不会没有西厢房的。我怀疑紧邻我们老院的西边的大院,以前会不会就是它的西厢房。因为西边这座大院,非常狭窄,两侧的房子也都很窄小,中间的走道,痩得仅能走一个人。会不会是依托我们老院的西厢房,改造而成了现在的样子。当然,这只是我的揣测,没有一点儿依据。
的东厢房,非常齐整,我小时候,一溜儿东厢房,足有十五间之多。这一条从前院直通后院的过道,笔直而悠长。我家就住在东厢房最里面的三间。据说,那三间房子,曾经是主人家的厨房。那时候,整座大院就一家人住,厨房显得宽敞气派。我家刚搬来时,最里面的一间还有残存的灶台,拆除灶台时,我爸发现埋在灶台下面的几块长条形的金闪闪的金属,以为是金条呢,喜出望外地拿到银行一验,空欢喜一场,不过是黄铜而已,是当年为祭祀灶王爷图个吉利的把戏。读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学放学时走进走出我们大院,经过这条长长的甬道,要走老半天;那时候常有一个女同学到我家来玩,一路各家窗户里扫射出来的目光,纷纷落在身上,越发觉得心重路长。
我家房子的南端,是全院的公共厕所。厕所只有两个蹲坑,但外面有一条过道,很宽阔,显示出当年的气派来。过道足有四五米长,最前面有一扇木门,里面带插销,谁进去谁就把插销插上。我们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在每天早上厕所最忙的时候,跑进去占据了位置,故意不出来,让那些敲着木门的大爷们干着急没辙。我们管这个游戏叫作“憋老头儿”,是我们童年最能够找到乐子的游戏。厕所过道的那一面涂成青灰色的墙,是我家的南山墙,成了我们孩子的黑板报,大家在“憋老头儿”的时候,用粉笔或石块往上面信笔涂鸦。通常是画一个长着几根头发的人头,或是一个探出脑袋的乌龟,然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大字:某某某大坏蛋,或某某某喜欢谁谁谁之类。写了擦,擦了写,一拨拨新起的小孩们前赴后继。
读高一那一年,学习淘粪工人时传祥,我还背着挺沉的木粪桶,跟着时传祥一起到我们大院的厕所里淘过粪。
厕所过道的东头,有一个很小的夹道,对着我家的后墙,那里堆放着杂物和碎砖乱瓦,越堆越高,从那里可以很轻巧地就爬上房顶。站在房顶上,前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甚至再远处的西山,都能够一眼看得见。国庆节夜晚燃放礼花的大炮,也能够依稀望得见。国庆节的晚上,我们早早地坐在房顶鱼鳞瓦的上面,静静地等待着突然的一声炮响,五彩缤纷的焰火腾空而起。在下一次礼花腾空之前的空隙中,弥漫在蒙蒙烟雾的夜空中,会有白色的降落伞像一个个白色的小精灵向我们飘来,那是礼花中的一部分。国庆节的时候,常常会有东南风,因此,那小小白色的降落伞,总能够缓慢地向我们飘来,飘过我们的房顶的时候,我们只要一伸手就能够把它们够下来。当然,也会有调皮的孩子用竹竿捷足先登把它们够了下来,惹得大家一通大呼小叫和下面大人的一通责骂之后,只好等待着下一次礼花的腾空而起。
十一年前,2005年,我回粤东会馆特意看它时,竟然看见当年立在影壁旁的那块石碑,垫在老街坊盖的小厨房的下面,露出一小截花岗石,像是千年乌龟探出的头。
六年前,2010年,却只剩下了粤东会馆的大门。我走进大门,只到原来的二道门的地方,就被围栏给挡住了,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一起也被挡在里面了,里面已经完全被拆得一片凋零。
前不久,我又去了一趟,围栏没有了,前面建起一座红漆大门,紧挨着老院的那扇已经斑驳沧桑的黑木门,仿佛让历史和现实故意做对比似的,那么触目惊心地不谐调。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红漆大门只能是官府人家的宅院。自以为是的现实,就是这样粗暴地改写历史旧貌。
透过门缝,望着簇新却空无一人的院子愣神的时候,从东跨院里走出来一位妇女叫我的名字,一看是老街坊。她告诉我,除了东跨院三户人家没有搬走,其余全部拆干净了,院子里都盖起了灰瓦红柱的新房。我遗憾地对她说这回看不成了。她把我请进她家,顺手把紧靠后窗的床铺的褥子掀开,又搬来一把椅子,放到后窗外,让我踩着床铺跳窗而进,一睹大院新颜。
我从这个小小的后窗跳了进去。空荡荡的院子,空荡荡的房子,过去历史曾经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已经不存在。我打开虚掩的房门,走进我原来住的那三间东房里,簇新的砖瓦、簇新的玻璃窗、水泥地,夕阳正透进来,将房前那棵老槐树斑驳的枝影打在地上。一切的景象仿佛不真实似的,像是置身在戏台上那样恍惚。不知它以后的用场,也不知以后要住什么人。
如果说第一座粤东会馆没有了,是历史的原因;后两座粤东会馆,却完全是这些年在我们的手上毁掉的。三家粤东会馆,四百多年历史,就这样如水长逝。
站在静悄悄、空荡荡的院子里,地理和历史的空间,只有依托记忆、依托想象、依托文字,依稀还在,现实的空间已经面目皆非。我想起了,想起了那些我曾经熟悉的已经过世的前辈和与我一样依然在世的人们,想起那些让我怀念让我心痛让我惋惜让我愤怒的种种人物。在人物与老院共生的漫长岁月的沧桑变化与动静对比中,重想杜诗:“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意味深长,不觉无言。
2016年3月9日写毕于布卢明顿细雨中
-
他不是孤儿!他竟是京圈太子爷?全文免费完整版阅读_一小只川渝暴龙_他不是孤儿!他竟是京圈太子爷?最新章节更新全集
他不是孤儿!他竟是京圈太子爷?小说是作者一小只川渝暴龙创作的精彩小说,窝棚文学网为您提供内容阅读。讲述了:【无系统+都市文+爽文+单女主+恋爱日常+清冷校花+神豪+顶级富二代+甜宠+不虐轻松】江晏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生,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每天放学后还要去工作挣房租和学费可突然有一天一个最不可能跟江晏产生交集的人出现了。林婉清!学校顶级女神,几乎是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林婉清:“我要跟江晏做同桌”。江晏:“啊?”。林婉清:“我要跟江晏一起吃饭上学”。江晏:“啥?”。林婉清:“我要跟江晏一起住”。江晏:“啊????”。就在江晏以为事情就会这样发展的时候,结果突然有一天亲爸亲妈找上门了,我成顶级富二代了?还是最顶级的那一批??。亲爸是全国知名企业江淮集团的总裁,流动资金何止上千亿。而亲妈家则是跟全国的政治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钱+权都有,这不起飞了?。等到众人发现我的身份时,不禁全都惊掉了下巴。李瑶:“江晏,你....你怎么会是....”。“江晏,我喜欢你,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之前我都是为了考验你对我的真心才会这样的啊~”。江晏见此只是笑着摇了摇头,没有说话。转过身牵起了校花的手。.....多年以后。江晏坐在客厅,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起玩耍,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简介无力,请移步正文)
-
人生,易如反掌全文免费完整版阅读_单车散人_人生,易如反掌最新章节更新全集
人生,易如反掌小说是作者单车散人创作的精彩小说,窝棚文学网为您提供内容阅读。讲述了:作为首富之子,上一辈子,我爱错了人。可这辈子,我不会再将错就错。面对为救情夫吧把我打成植物人的老婆,以及和她一起夺取我家业的情夫,最后,还让我惨死在养老院里!面对这两人,我怎么会心软呢?这辈子,我拿他们开刀,让他们两个狗男女血债血偿!
-
重生:村里有个老汉是神枪手全文免费完整版阅读_杨三斤啊_重生:村里有个老汉是神枪手最新章节更新全集
重生:村里有个老汉是神枪手小说是作者杨三斤啊创作的精彩小说,窝棚文学网为您提供内容阅读。讲述了:他带着无尽的忏悔与遗憾,意外穿越时空,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东北农村。那是一个充满原始野性魅力的时代,枪支与狩猎尚未被禁止,物资的匮乏与自然资源的丰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 ,这句流传的俗语,正是当时生活的生动写照。在这片黑土地上,留守妇女们为了能让生活多些滋味,有着属于她们的故事。而他,怀揣着上一世的不甘,背负着象征勇气的牛角弓,一头扎进了银装素裹的北林雪原。他凭借着刻在骨子里的狩猎本能与丰富经验,将那些野兽横行的深山老林、荒寒的北荒雪原,统统变成了自己的 “私人领地” 。在这里,他与野猪搏斗,教训嚣张的黑熊,在河流中捞鱼捕虾,每一次行动都是与大自然的亲密对话。不仅如此,他没有忘记家庭的责任。他用狩猎所得,精心侍奉父母,让妻子女儿也能尽情享受美食,在这艰苦的岁月里,为家人撑起一片富足温暖的天空,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热血与温情的生活篇章。
-
先婚后爱:冷面霸总每天撩爆我全文免费完整版阅读_金秋_先婚后爱:冷面霸总每天撩爆我最新章节更新全集
先婚后爱:冷面霸总每天撩爆我小说是作者金秋创作的精彩小说,窝棚文学网为您提供内容阅读。讲述了:隐婚三年,我是身份尊贵的总裁夫人,却几乎没人知道。白天我是家境普通的女人,晚上我却享受着别人梦想中的生活。我原本以为他只能给我物质上的享受,却没想到打架时有他撑腰,受了委屈有他轻哄。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小媳妇竟然还有个马甲?
-
别酸了!这次我真遇到官配了全文免费完整版阅读_山楂煮茶_别酸了!这次我真遇到官配了最新章节更新全集
别酸了!这次我真遇到官配了小说是作者山楂煮茶创作的精彩小说,窝棚文学网为您提供内容阅读。讲述了:在那段青涩的校园时光里,他的世界几乎被她填满。他满心欢喜地围绕在她身边,小心翼翼地经营着那份懵懂的喜欢,以为这份执着终能换来圆满的结局。终于,在那个被暗示告白的夜晚,他怀揣着紧张与期待,却被她冰冷的话语瞬间击碎——“没有几万块的包包,不够诚意。” 那一刻,他多年的深情如泡沫般破碎,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只能草草收场。心灰意冷的他在命运的安排下,邂逅了高冷的校花学姐。一次意外,学姐将他带回了家,原本两条平行的人生轨迹,自此开始紧密纠缠。生活在一起后,他发现了学姐截然不同的一面。在静谧的夜晚,她会在梦游中迷糊地抱着他的腰,轻声呢喃 “抱抱”;在疲惫的时刻,她会睁着清澈的眼睛,温柔地请求:“帮我吹头发。” 学姐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依赖与温柔,让他彻底沦陷。后来,她看到他与学姐手牵手漫步校园,嫉妒瞬间将她吞噬。她红着眼睛,带着一丝不甘与期盼,问道:“能不能再喜欢我一次?”